一百個人學琴,有一百種理由。而對香港小朋友來說,有種學琴叫「爸爸媽媽叫我學」。
來到琴室的小朋友,我總先叫他的名字,然後問他多少歲,或者挑兩個最喜歡的琴鍵。從這一刻開始觀察他的性情:內向、活潑、自主性強?一句對那位學生太重的指示,足夠讓那節課堂陷入無盡頭的拉鋸與抗拒。音樂老師的自我修行,從選擇當下的教法,並觀察小朋友學生的反應開始。
我是一位主力教小朋友的兼職鋼琴老師,同時斜杠各種相關與不相關的工作維生。我的日常是在琴室等待學生來到,然後在課堂引導小孩學習音樂基礎知識、閱譜彈奏,以及培養音樂感和說故事的能力。我教授的學生,主要是四至九歲的小朋友,大部份都是國際學校學生,來自相對富裕的家庭。
縱觀行業,最常見亦最穩定的工作模式,是連鎖琴行的全職音樂導師。前幾年有人戲稱,連鎖琴行用譚仔(香港一知名連鎖食肆)月薪價錢聘請音樂導師,還是六天工作;他們的要求亦不低,門檻是修讀音樂系,又或者考獲演奏級。至於非連鎖的小型琴室,多數是安排數日時間,由琴行接學生,穩定性較低,薪金以時薪計算,好處是時間彈性,導師要跳出來自己接學生也相對容易。
為求多賺一點,不用與琴行分成,很多鋼琴老師都在累積經驗和潛在學生群之後,自行接學生,上門教琴,又或者租借琴室教學。亦有些老師創業,成立工作室,聘請更多老師,以特定的教學理念和市場定位吸引學生群。
同一個行業,不同的工作模式和對象,很影響老師和學生的體驗——我的經歷也只是冰山一角。有些琴行以考試主導,比較着重訓練學生考級,甚至被稱為擁有八級鋼琴資歷的「讀譜機器」,在那裏學琴的話,有點像看醫生,對症下藥,藥到病除,老師面對考試體制和家長的壓力,很多時少不免催谷學生。新創琴行視乎教學理念和管理風格,可以很自由,可以很脫離「坐定定」的傳統教育想像,相對以學生為本,讓每個學生都以適合的方式享受學琴——就算不想學的話,至少來到的時候並不痛苦。
至於家長的心態,希望子女考個八級綱琴、拿取證書報學校的當然常見;即便不望子成龍,家長也多少對子女有點期望。學琴不便宜,看着成果遙遙,家長就算不求考級、勝出比賽,也多少希望子女至少爭氣聽話一點,上課時好好專注。
說到我,其實我喜歡教琴的理由很簡單。我喜歡鋼琴,又剛好找到這個用自己方式影響別人的空間。但簡單的東西,守護起來很困難。外部壓力、行業不穩、教學裡面種種磨蝕和消耗自己的事,每一節課都像是一種修行。

暗自羨慕學生的主見
我教授的學生,大部分來自國際學校,用英語溝通。他們可以戴頭飾上學,也可以塗紅唇膏,不會被視為違反校規或儀容不整。
我出身於主流學校,成長於權威式的教育,與他們相處,就好像與一種自己不可能擁有的童年相處。他們沒有被體制教育成「坐定定」的乖小孩,而是擅於發表己見,會提出請求,甚至習慣與老師商量做法,而非被動接收指令。比如說,他們進來琴房,不一定會直接坐到琴前,而是東眺西望,問這個是甚麼、那個是甚麼。著他們彈上次學過的歌,可能會彈另一首更加喜歡的歌,還會問我有沒有聽過、能不能教他們喜歡的歌。
羨慕的心情我固然有,畢竟他們能夠擁有的教育,以及因此擁有的自信和自主意識,並不是長大後能輕易靠自己調整而得。相較於傳統學校出身的學生,他們好像多了一份創意和靈動,沒有一種絕對服從的壓抑感。
當然,不論背景,小朋友總有不聽從指示、有情緒的時候,但憑觀察所見,他們表達意願的時候,會認為自己的想法是「正當」的,而非只是「不想聽話」。他們不會說「我不要做」,而是說「我不是跟你說過我不喜歡嗎?我說過我喜歡彈的是這首。」不喜歡做某件事的時候,他們會直接提出或者「討價還價」。
身為老師,我當然要維持應有的規矩,指正他們自創而無效的學習方法。不過,在老師的身份背後,我時常都會暗自欣賞他們擁有主見之餘,毫不費力便能直接表達需要,不會盲目服從,對自己喜歡的事物又能堅持到底。比如有學生希望學習吉他而非鋼琴,於是跟我商量「可以一半時間是學習吉他,一半時間學習鋼琴嗎?」在很多人的童年,根本連擁有這種想法的空間都沒有吧。
我基本上是以尊重學生需要、允許創意的角度出發;溝通方式方面,非批判、讚美、欣賞的態度,幾乎總是比責罵和威脅奏效。我曾經在外國生活一段時間,受西方的讚美文化影響,很自然便能夠動用「稱讚模式」,即使學生有些地方彈得不太好,也可以在指正之後,稱讚他們有所改善的部份。
小朋友能夠輕易感受到大人真誠與否,因此想要做一個怎樣的老師,便要努力成為怎樣的人。然而,面對本地學生我也常感到難以啟齒稱讚,尤其是使用廣東話教學。記得有次教四歲的小朋友學生,平常用英語稱讚學生彈得好的說話,譯成廣東話之後便說不出口。
在華人教育裏面,我們有多常聽見別人用誇張的聲調說「嘩,你做得真好」?因為沒有聽過太多,自然也說不出口,硬要說也毫無真誠可言。

「惡」的疑惑
以鼓勵代替責罵,說起來像是陳腔濫調,真正實踐起來,卻是一場覺察和轉化的成長考驗。多年教育養成的習性,仍是會上課當下的教學判斷中,內心容易冒出惡魔的聲音。
很多次在學生不跟隨指示演奏,或是一再把話題轉到非音樂相關時,我內心感到拉扯。看着學生要彈不彈,或者用手掌亂按時,「快少少得唔得呀大佬?」心裏的一句冒出頭來,我內心浮躁,有種進度停滯的焦急,但我還是深呼吸一下。
每個學生適合的教學方式不一樣,「惡啲」(兇一些)是不是有需要?有時可能是,但無論如何,沒有一種學生需要承擔老師的氣餒或不知所措,這是老師擁有權力應有的自覺。
我小時侯學琴,試過被老師質問「到底在彈甚麼」,不斷要求解釋,而我其實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彈得很不好,只為被質問而感到恐懼和委屈。到現在做老師,便明白有時學生彈得很好,可能是那天早上收到好消息後心情輕快;學生不聽指示、感到煩躁,是需要觀察一下學生的身體語言想表達甚麼。可能是當天多活動,身心疲累?可能是教材太難或太簡單,要換一首歌?又或者是他們進入了學習的挫折期,可以問問他們喜歡甚麼歌,投其所好?又或者是他們與我或者學了很久的同伴比較,認為自己彈得不好而感到氣餒?
當然,也有可能是他們從一開始就沒有興趣,勉強沒幸福。
在華人文化裏面,身為老師若沒有讓學生乖乖聽話,是很「失威」的,更有機會被誤會是年輕、未有經驗而「不夠惡」。當自己內化「老師應該有能力控制學生」的想法,若有學生沒有跟隨自己的指示時,很容易就他們不受控而憤怒。
但我慢慢明白到,我們是想快快達到目的,卻又屢試不果,所以才感到不耐煩,甚至想要指責學生。我做不到總是一臉愛心的模樣(而且也沒有必要),但小朋友也是人,老師放下控制他人的執念,自然不會那麼容易感到焦躁。
那究竟要不要惡呢?懂得發惡是老師必備的生存技能,因為學生在做危險之事或者傷害他人時,懂得即時喝止是必要的。我希望自己能夠「該惡時惡」,而不是平常必須保持威嚴。無法感到欣賞和想讚美時,至少選擇慎言:不批判學生的創意,也不批判他們整個人。如果不用靠威脅和指責,而是在適當的限制下給予指導和啟發,他們便會自發學習,那為甚麼要靠惡呢?
就學生的背景或家庭教育而言,他們比較放開自己、不會「坐定定」是十分能夠理解的,同時這也是我喜歡教這類學生的原因。從教學的成效來看,制止學生所有非課堂相關的行為,也多半不會提升學習成果,比如他們要是離開琴椅四處走動,可能是他們確實需要活動一下,強迫他們坐下整個小時,也不等同有接收到我所教的。學生喜歡畫畫,那可以從畫音符開始認音,而非執着要學生按設計好的方法學習。如果他們喜歡某首流行曲,也可以試着一起分析歌曲特色。
然而,在保守的教育底下成長,放不開的倒是我自己——課堂裏面到底能有多大的自由度?當他們的舉動,在我的童年裏面說會被師長責罰、阻止,那現在身為老師,我不阻止同樣的行為,內心也會感到混亂,就像是當年的自己淘氣了,卻沒有被責罰的落差感。
我遇過一個八歲的男生,時常提出一些條件,比如必須讓他們在琴譜上畫畫,才會願意配合彈奏,甚至用威脅式的語言,例如「如果你不答應我這個請求,我就不會再上這一節課!」我一方面盡量以學生的喜好為切入點,同時亦明白不能隨意答應他的請求,以免他認為底線是可以退讓。
也許在華人教育中沒有太多「有規矩地允許自由」的師長作榜樣,我發現要成為一個鼓勵創意、不壓抑學生自我的教育者,靠的不是心態的轉換,而是要重新學習如何有界線地給予學生自由。

彈琴的對與錯
較為開放的教育風格看似美好,實際上執行卻困難重重——沒有一種教育方式是魔法棒。
教導四歲小朋友和比較有主見的小朋友,是最有挑戰的。四歲的小朋友肌肉發展尚未到位,理解能力相對較弱,處於比較需要認同、會嘗試不同做法的年齡,也傾向不聽從指示。最難的不是他們有自己的做法,而是他們的專注力和肌肉發展仍在發展階段,而且尚未完全擁有「上課要聽老師說話」的自覺,四歲更不是可以講大道理的年齡階段。
他們喜歡用拳頭代替手指按琴鍵,又或者用手肘一次按很多個琴鍵,又或者刻意不按指引他們按的琴鍵,反倒彈其他音。
記得有一次,我讓小朋友按下特定琴鍵,而他刻意按下其他琴鍵,我靈機一觸問他「這個琴鍵代表甚麼動物?是代表貓嗎?」小朋友高興地點頭示意,避免了對立的關係,同時也建立了可用於教學的共通語言。
慢慢地,我不會馬上跟學生糾結對錯,而是把學習變成遊戲,要彈特定的音符才能過關,甚至和我鬥快,讓他們想要完成任務。說到底,小孩子不是想要對抗,而是想嘗試其他做法,被大人看見和認同。我不會認同和鼓勵不合適的彈法,但希望讓他們明白:這個空間可以試錯,我有看見(acknowledge)他們的嘗試。而在此過後,我們嘗試用另一種更好的方式去做,按照更適合的指法和看譜方式去演奏。
給予空間絕對不等於放縱,更多時只是不急着反應,允許亂按一通的琴聲,以及多次彈錯歌曲的氣餒,在琴房多存在幾秒鐘。有些學生很害怕彈錯音,彈得小心翼翼,好比按錯就會失分。我看在眼內,當自己示範彈奏時偶爾彈錯,就淡然地說一句「噢,錯了,再來一遍」,希望讓彈錯音變成平常不過的事,從中感受到琴房是有空間試錯的。
但身為鋼琴老師,我想學生放心試錯,知道什麼是錯,又不想讓他們太知道什麼是對。音樂的對錯如何界定?古典音樂是殘酷的,演奏最不容錯。我有時跟朋友閒聊時笑說,鋼琴家練了二十年,都在練那個F音可以怎樣彈出十種不同的音色,而在比賽時把F音彈成了G音,那是無論如何都說不過去的致命傷。
說「彈錯不緊要」,有時只是句舒緩緊張的鼓勵說話而已,演奏古典音樂的難處是彈錯真的不允許。但彈對也不等於彈得好,而一味害怕彈錯,便失去了音樂的表達力。
技術要練得好,努力到毫不費力,同時心理質素要強,在基本技巧之上加上音樂感,甚或自我表達,這樣才能稱得上是好的演奏。純熟運用技巧也能彈出富有音樂性的演奏,但裡面有沒有自我風格的表達,用心聆聽仍是能聽出來。
我主要教授古典音樂,但內心住了一顆即興演奏的奔放內心,會接觸比較隨興的音樂派別,平時喜歡即興彈奏任意旋律,讓自己放空,就像隨手在紙上塗鴉一般。即興演奏沒有絕對對錯,沒有古典音樂般嚴謹的規則,即使是本身有主旋律的即興流行曲伴奏或者爵士樂演奏,只要大致遵從基本的樂理隨便按和弦,也能夠自由地彈出好聽的音樂。
教學時,我也會跟學生即興演奏。有些學生會很怕做錯,又或者因為未彈到心目中的水平而感到挫敗,但即興演奏沒有對錯,能保有一點點不被批判的空間,既培養學生的音樂感和成就感,也能與學生建立連結、給予他們心理安全感。
最重要的是,讓學生重新感受音樂,重新感受自己。

害怕「失禮」的家長?
當然,選擇如何教從來不只是學生和老師之間的事,而是老師、學生、琴行,與家長的張力。琴行定義了教學的方針是考試為主、專業導向還是培養音樂造詣,決定行政安排如請假的政策、補堂安排。家長則視乎他們對子女的期望、對教學風格有否特定偏好、有多關心進度之類。
年紀愈小的學生,我就愈需要與家長站在同一陣線,尤其四、五歲的學生。有時候家長在場旁觀,與家長合作課堂能更加順暢。但比較想表現自己的學生,注意力可能會放在尋求父母認同,反而比較難集中。有時候家長和我共同教學,小朋友也有機會嘗試挑戰權威,或者故意不服從。
對不少家長來說,小朋友有否「失禮」是個重要的事情。四、五歲的小朋友喜歡探索,不會全按着指示學習鋼琴,而家長有時會在意自己的小朋友「唔比面」(不給自己面子),比如在琴上用拳頭亂按,又或者是故意用相反的次序彈奏音符。很多家長問,「是不是每個小朋友都會這樣(不聽指令、亂按琴鍵)?」
愛子心切,或許每個家長都會擔心自己的小朋友是不是特別不聽話、很「難搞」,或者擔心自己的兒女為他人添了麻煩,表示不好意思。這些問題背後,可能是家長想知道孩子是否正常發展,或者擔心孩子學得不好。事實上,我早就習慣了學生在課室上扮貓、扮獅子,問我能不能做拱橋和倒立,或者試圖用手肘或鼻子彈琴,不斷即興彈奏說要教我怎樣彈、叫他試彈A音卻刻意彈C音試探反應。
只要小朋友來到,人還坐在琴椅上、用雙手彈琴,我都不會感到特別驚訝或難處理。我當然會盡力引導,但他們不跟從指示,也是意料之內,這是他們成長的過程,時間久了自然會有所改變。如果他們四、五歲,卻完全聽命於我,甚至表現出很害怕不聽話會被責罵,我反而會好奇他們是不是有不好的經歷。
其實老師的主要職責,正正是面對眼前的小朋友,觀察他們對指示的反應,思考怎樣引導他們,建立音樂感和肌肉記憶。我不會期望學生要聽話、有禮、尊師重道,那些都是大人的禮儀,來到琴行最重要是給予空間去探索和嘗試,用最適合的方式教學。我才不會認為他們失禮甚麼的,小朋友不聽家長或老師的話,也不等於家長沒有好好管教。
我曾遇上一位五歲的小男孩,每次上課都不會回應我的說話或者跟隨指令彈琴,而是不斷做其他不相關的事情,或者把話題拉到別處。我最初也暗自焦急,每節課用不少時間試圖讓他乖乖按指令學琴。後來我又教他新的歌曲和樂理知識,但感覺對牛彈琴,他還是照舊四處走動、問各種不相關的問題。
但過了一段時間,他忽然回到鋼琴前,用正確的方式演奏了整個樂曲。這讓我明白,即使他可能完全沒有表現出在聆聽,甚或表現得不感興趣,課室上說的話他都有默默吸收,他想要回來彈琴是就能夠運用所學。於是我每節課都照樣教授內容,減少跟他拉据,盡量輸出教學內容,等到某一個時刻,他可能又會忽然進步。
我從中學會,有沒有「聽我講」的執着是可以放下的,最重要是他對鋼琴有興趣、學習也有所進展。

現實煩心事
說了那麼多夢幻的話,也說說比日常上課所見更現實的事——薪金與穩定性。教琴是手停口停的工作,學生來了就有學費,學生不來就沒有。
一年五十二週,學生時代最期待的暑假、打工仔最期待的聖誕、新年,是自僱教琴老師面對學生請假甚至流失的時候。我本身已是斜槓族,對公眾假期沒太大興奮感,教琴之後,更是抗拒長假期。我有時會乾脆先發制人,預先在學生大概都不來的日子請假,好讓心理好過一點,製造「是我請假不是你們請假」的感覺。於會乎,再多學生也好,一年到頭總會有一兩個星期沒工開,這段時間找其他短期工作幫補,又不是易事。
雖然教琴時薪高,但黃金時段給了教班,基本上當天很難安排其他固定長時間的工作。我最初教琴,因有其他較固定的兼職幫補,加上教琴初期學生數量少,收入本身就不多,學生請假也沒有太大影響。到後來教琴佔工作組合的比重更大,面對兩星期內大部分學生都請假,確實會感到焦躁和不安:一方面失去平時生活的規律、節奏,另一方面看着收入減少,更甚的是怕學生停了一兩個星期沒學,失去學習熱情。
身為鋼琴老師,我怕學生流失,也同樣在心底裏面害怕自己會洩氣。
跟所有職業一樣,日子久了,難免會碰到煩心事。再珍惜與學生的點滴也好,好些時候付出是不會得到回饋的。又或者說,用心教學是我的事,學生學不學、學得如何是學生的事。有很多的不辭而別、學生衝口而出的言語,也會讓負面情緒累積。到學生請假的時候,有了空檔,那些灰心與冷意就好像找到空間去浮現。
教琴數百元一堂,沒有想像中的好賺。只叫學生「自己彈一次」,再指出錯音作罷的老師比比皆是,而有心的老師,習琴十數年,不斷摸索教學手法和持續進修,所花的時間和專業性,也絕對值得一份能夠糊口的薪水。「一千元一小時的鋼琴老師」只是特例,這個行業裡多數老師需要同時承接不同類型的工作維生;即使花上一兩年在琴行累積學生或自行招生,也始終無法解決薪金不穩定的結構性問題。
更甚的是,要有更穩定的薪金,又或者新晉琴室需要在市場生存,也難免要迎合市場需要。教國際學生或許能以興趣為先,但相對於一些旨在考級的本地學生,前者的退學率較高,累積穩定學生群需時更長,後者則因為要考級,不會輕易退出,自然比較容易留客。

I want you to be happy
直至我開始教琴前,鋼琴就像我人生的佈景版——抬頭一看,他從來都在,卻從沒成為過人生的主軸。入行時我全不抱期望,做着做着發現不錯,問我為甚麼教琴的話,除了是對鋼琴的喜歡,還因為在教學中收獲了種種緣份和自我啟蒙。
自出生,家中已有一台鋼琴,兩三歲時我便會自行嘗試彈出聽過的歌曲,到三四歲便開始學琴,一學便學了十三四年。因着少許天份,音樂成為我小時候的優越感所在,總是想要表現自己,收到讚美就會沾沾自喜。長大一點,直到中四、五,我總是把握在校內彈琴的瞬間,暫時脫離群體社交,專注在當下的演奏獲得一絲平靜。
學琴十數年,前面至少十年,我都不明白音樂是甚麼,只是按技巧在琴鍵彈奏。事實上,那些年長期被學業壓得喘不過氣,處於心靈麻目的狀態,不要說用彈琴表達自我,很多時候連自己有甚麼感受都不知道。
轉捩點是中五的一次演奏級考試。那次考試不合格,考官在紙上寫上「技術上達標,但聽不到任何音樂」。我才第一次直面音樂是甚麼,迫着思考在練習技術之餘,自己想透過音樂表達甚麼。
重考那次,考官在開始時跟我說,「我想你是開心的(I want you to be happy.)」,說我可以想像自己在開音樂會,而他是觀眾。就這樣,我重考合格了,自始彈琴對我來說再也不是追求好不好聽,而是心靈觸動和連結。後來我去旅行看見公共鋼琴,又或者在本地咖啡店看到鋼琴,都會上前彈奏。曾有咖啡店主跟我說,有很多客人聽到彈奏的音樂都哭了,當刻忽然明白:比起得到獎聲,有人聽了我彈奏的音樂而感到治癒,才是真正讓我感到滿足的事。
現在我教琴,有時仍想摸索自己還有多少演奏的渴望,還是只想要為他人保有學習演奏的空間?唯一可以肯定的是,我想誠實面對自己的渴望:我和那些彈完一首歌,轉頭看着我的學生如出一轍,內心都住着一個想被認同和被理解的小孩。
(為保護學生隱私,文中提及的學生故事經修改和模糊化處理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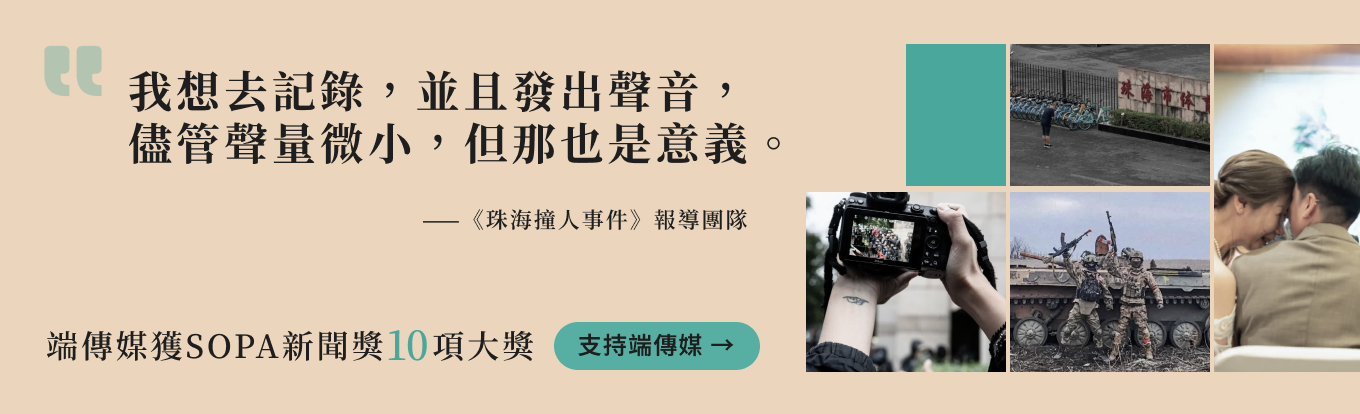



我讀你的文字很有被觸動的感覺,因為你很真誠地坦露你的想法,而這些想法往往令我感到很溫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