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百个人学琴,有一百种理由。而对香港小朋友来说,有种学琴叫“爸爸妈妈叫我学”。
来到琴室的小朋友,我总先叫他的名字,然后问他多少岁,或者挑两个最喜欢的琴键。从这一刻开始观察他的性情:内向、活泼、自主性强?一句对那位学生太重的指示,足够让那节课堂陷入无尽头的拉锯与抗拒。音乐老师的自我修行,从选择当下的教法,并观察小朋友学生的反应开始。
我是一位主力教小朋友的兼职钢琴老师,同时斜杠各种相关与不相关的工作维生。我的日常是在琴室等待学生来到,然后在课堂引导小孩学习音乐基础知识、阅谱弹奏,以及培养音乐感和说故事的能力。我教授的学生,主要是四至九岁的小朋友,大部份都是国际学校学生,来自相对富裕的家庭。
纵观行业,最常见亦最稳定的工作模式,是连锁琴行的全职音乐导师。前几年有人戏称,连锁琴行用谭仔(香港一知名连锁食肆)月薪价钱聘请音乐导师,还是六天工作;他们的要求亦不低,门槛是修读音乐系,又或者考获演奏级。至于非连锁的小型琴室,多数是安排数日时间,由琴行接学生,稳定性较低,薪金以时薪计算,好处是时间弹性,导师要跳出来自己接学生也相对容易。
为求多赚一点,不用与琴行分成,很多钢琴老师都在累积经验和潜在学生群之后,自行接学生,上门教琴,又或者租借琴室教学。亦有些老师创业,成立工作室,聘请更多老师,以特定的教学理念和市场定位吸引学生群。
同一个行业,不同的工作模式和对象,很影响老师和学生的体验——我的经历也只是冰山一角。有些琴行以考试主导,比较着重训练学生考级,甚至被称为拥有八级钢琴资历的“读谱机器”,在那里学琴的话,有点像看医生,对症下药,药到病除,老师面对考试体制和家长的压力,很多时少不免催谷学生。新创琴行视乎教学理念和管理风格,可以很自由,可以很脱离“坐定定”的传统教育想像,相对以学生为本,让每个学生都以适合的方式享受学琴——就算不想学的话,至少来到的时候并不痛苦。
至于家长的心态,希望子女考个八级纲琴、拿取证书报学校的当然常见;即便不望子成龙,家长也多少对子女有点期望。学琴不便宜,看着成果遥遥,家长就算不求考级、胜出比赛,也多少希望子女至少争气听话一点,上课时好好专注。
说到我,其实我喜欢教琴的理由很简单。我喜欢钢琴,又刚好找到这个用自己方式影响别人的空间。但简单的东西,守护起来很困难。外部压力、行业不稳、教学里面种种磨蚀和消耗自己的事,每一节课都像是一种修行。

暗自羡慕学生的主见
我教授的学生,大部分来自国际学校,用英语沟通。他们可以戴头饰上学,也可以涂红唇膏,不会被视为违反校规或仪容不整。
我出身于主流学校,成长于权威式的教育,与他们相处,就好像与一种自己不可能拥有的童年相处。他们没有被体制教育成“坐定定”的乖小孩,而是擅于发表己见,会提出请求,甚至习惯与老师商量做法,而非被动接收指令。比如说,他们进来琴房,不一定会直接坐到琴前,而是东眺西望,问这个是甚么、那个是甚么。著他们弹上次学过的歌,可能会弹另一首更加喜欢的歌,还会问我有没有听过、能不能教他们喜欢的歌。
羡慕的心情我固然有,毕竟他们能够拥有的教育,以及因此拥有的自信和自主意识,并不是长大后能轻易靠自己调整而得。相较于传统学校出身的学生,他们好像多了一份创意和灵动,没有一种绝对服从的压抑感。
当然,不论背景,小朋友总有不听从指示、有情绪的时候,但凭观察所见,他们表达意愿的时候,会认为自己的想法是“正当”的,而非只是“不想听话”。他们不会说“我不要做”,而是说“我不是跟你说过我不喜欢吗?我说过我喜欢弹的是这首。”不喜欢做某件事的时候,他们会直接提出或者“讨价还价”。
身为老师,我当然要维持应有的规矩,指正他们自创而无效的学习方法。不过,在老师的身份背后,我时常都会暗自欣赏他们拥有主见之余,毫不费力便能直接表达需要,不会盲目服从,对自己喜欢的事物又能坚持到底。比如有学生希望学习吉他而非钢琴,于是跟我商量“可以一半时间是学习吉他,一半时间学习钢琴吗?”在很多人的童年,根本连拥有这种想法的空间都没有吧。
我基本上是以尊重学生需要、允许创意的角度出发;沟通方式方面,非批判、赞美、欣赏的态度,几乎总是比责骂和威胁奏效。我曾经在外国生活一段时间,受西方的赞美文化影响,很自然便能够动用“称赞模式”,即使学生有些地方弹得不太好,也可以在指正之后,称赞他们有所改善的部份。
小朋友能够轻易感受到大人真诚与否,因此想要做一个怎样的老师,便要努力成为怎样的人。然而,面对本地学生我也常感到难以启齿称赞,尤其是使用广东话教学。记得有次教四岁的小朋友学生,平常用英语称赞学生弹得好的说话,译成广东话之后便说不出口。
在华人教育里面,我们有多常听见别人用夸张的声调说“哗,你做得真好”?因为没有听过太多,自然也说不出口,硬要说也毫无真诚可言。

“恶”的疑惑
以鼓励代替责骂,说起来像是陈腔滥调,真正实践起来,却是一场觉察和转化的成长考验。多年教育养成的习性,仍是会上课当下的教学判断中,内心容易冒出恶魔的声音。
很多次在学生不跟随指示演奏,或是一再把话题转到非音乐相关时,我内心感到拉扯。看着学生要弹不弹,或者用手掌乱按时,“快少少得唔得呀大佬?”心里的一句冒出头来,我内心浮躁,有种进度停滞的焦急,但我还是深呼吸一下。
每个学生适合的教学方式不一样,“恶啲”(凶一些)是不是有需要?有时可能是,但无论如何,没有一种学生需要承担老师的气馁或不知所措,这是老师拥有权力应有的自觉。
我小时侯学琴,试过被老师质问“到底在弹甚么”,不断要求解释,而我其实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弹得很不好,只为被质问而感到恐惧和委屈。到现在做老师,便明白有时学生弹得很好,可能是那天早上收到好消息后心情轻快;学生不听指示、感到烦躁,是需要观察一下学生的身体语言想表达甚么。可能是当天多活动,身心疲累?可能是教材太难或太简单,要换一首歌?又或者是他们进入了学习的挫折期,可以问问他们喜欢甚么歌,投其所好?又或者是他们与我或者学了很久的同伴比较,认为自己弹得不好而感到气馁?
当然,也有可能是他们从一开始就没有兴趣,勉强没幸福。
在华人文化里面,身为老师若没有让学生乖乖听话,是很“失威”的,更有机会被误会是年轻、未有经验而“不够恶”。当自己内化“老师应该有能力控制学生”的想法,若有学生没有跟随自己的指示时,很容易就他们不受控而愤怒。
但我慢慢明白到,我们是想快快达到目的,却又屡试不果,所以才感到不耐烦,甚至想要指责学生。我做不到总是一脸爱心的模样(而且也没有必要),但小朋友也是人,老师放下控制他人的执念,自然不会那么容易感到焦躁。
那究竟要不要恶呢?懂得发恶是老师必备的生存技能,因为学生在做危险之事或者伤害他人时,懂得即时喝止是必要的。我希望自己能够“该恶时恶”,而不是平常必须保持威严。无法感到欣赏和想赞美时,至少选择慎言:不批判学生的创意,也不批判他们整个人。如果不用靠威胁和指责,而是在适当的限制下给予指导和启发,他们便会自发学习,那为甚么要靠恶呢?
就学生的背景或家庭教育而言,他们比较放开自己、不会“坐定定”是十分能够理解的,同时这也是我喜欢教这类学生的原因。从教学的成效来看,制止学生所有非课堂相关的行为,也多半不会提升学习成果,比如他们要是离开琴椅四处走动,可能是他们确实需要活动一下,强迫他们坐下整个小时,也不等同有接收到我所教的。学生喜欢画画,那可以从画音符开始认音,而非执着要学生按设计好的方法学习。如果他们喜欢某首流行曲,也可以试着一起分析歌曲特色。
然而,在保守的教育底下成长,放不开的倒是我自己——课堂里面到底能有多大的自由度?当他们的举动,在我的童年里面说会被师长责罚、阻止,那现在身为老师,我不阻止同样的行为,内心也会感到混乱,就像是当年的自己淘气了,却没有被责罚的落差感。
我遇过一个八岁的男生,时常提出一些条件,比如必须让他们在琴谱上画画,才会愿意配合弹奏,甚至用威胁式的语言,例如“如果你不答应我这个请求,我就不会再上这一节课!”我一方面尽量以学生的喜好为切入点,同时亦明白不能随意答应他的请求,以免他认为底线是可以退让。
也许在华人教育中没有太多“有规矩地允许自由”的师长作榜样,我发现要成为一个鼓励创意、不压抑学生自我的教育者,靠的不是心态的转换,而是要重新学习如何有界线地给予学生自由。

弹琴的对与错
较为开放的教育风格看似美好,实际上执行却困难重重——没有一种教育方式是魔法棒。
教导四岁小朋友和比较有主见的小朋友,是最有挑战的。四岁的小朋友肌肉发展尚未到位,理解能力相对较弱,处于比较需要认同、会尝试不同做法的年龄,也倾向不听从指示。最难的不是他们有自己的做法,而是他们的专注力和肌肉发展仍在发展阶段,而且尚未完全拥有“上课要听老师说话”的自觉,四岁更不是可以讲大道理的年龄阶段。
他们喜欢用拳头代替手指按琴键,又或者用手肘一次按很多个琴键,又或者刻意不按指引他们按的琴键,反倒弹其他音。
记得有一次,我让小朋友按下特定琴键,而他刻意按下其他琴键,我灵机一触问他“这个琴键代表甚么动物?是代表猫吗?”小朋友高兴地点头示意,避免了对立的关系,同时也建立了可用于教学的共通语言。
慢慢地,我不会马上跟学生纠结对错,而是把学习变成游戏,要弹特定的音符才能过关,甚至和我斗快,让他们想要完成任务。说到底,小孩子不是想要对抗,而是想尝试其他做法,被大人看见和认同。我不会认同和鼓励不合适的弹法,但希望让他们明白:这个空间可以试错,我有看见(acknowledge)他们的尝试。而在此过后,我们尝试用另一种更好的方式去做,按照更适合的指法和看谱方式去演奏。
给予空间绝对不等于放纵,更多时只是不急着反应,允许乱按一通的琴声,以及多次弹错歌曲的气馁,在琴房多存在几秒钟。有些学生很害怕弹错音,弹得小心翼翼,好比按错就会失分。我看在眼内,当自己示范弹奏时偶尔弹错,就淡然地说一句“噢,错了,再来一遍”,希望让弹错音变成平常不过的事,从中感受到琴房是有空间试错的。
但身为钢琴老师,我想学生放心试错,知道什么是错,又不想让他们太知道什么是对。音乐的对错如何界定?古典音乐是残酷的,演奏最不容错。我有时跟朋友闲聊时笑说,钢琴家练了二十年,都在练那个F音可以怎样弹出十种不同的音色,而在比赛时把F音弹成了G音,那是无论如何都说不过去的致命伤。
说“弹错不紧要”,有时只是句舒缓紧张的鼓励说话而已,演奏古典音乐的难处是弹错真的不允许。但弹对也不等于弹得好,而一味害怕弹错,便失去了音乐的表达力。
技术要练得好,努力到毫不费力,同时心理质素要强,在基本技巧之上加上音乐感,甚或自我表达,这样才能称得上是好的演奏。纯熟运用技巧也能弹出富有音乐性的演奏,但里面有没有自我风格的表达,用心聆听仍是能听出来。
我主要教授古典音乐,但内心住了一颗即兴演奏的奔放内心,会接触比较随兴的音乐派别,平时喜欢即兴弹奏任意旋律,让自己放空,就像随手在纸上涂鸦一般。即兴演奏没有绝对对错,没有古典音乐般严谨的规则,即使是本身有主旋律的即兴流行曲伴奏或者爵士乐演奏,只要大致遵从基本的乐理随便按和弦,也能够自由地弹出好听的音乐。
教学时,我也会跟学生即兴演奏。有些学生会很怕做错,又或者因为未弹到心目中的水平而感到挫败,但即兴演奏没有对错,能保有一点点不被批判的空间,既培养学生的音乐感和成就感,也能与学生建立连结、给予他们心理安全感。
最重要的是,让学生重新感受音乐,重新感受自己。

害怕“失礼”的家长?
当然,选择如何教从来不只是学生和老师之间的事,而是老师、学生、琴行,与家长的张力。琴行定义了教学的方针是考试为主、专业导向还是培养音乐造诣,决定行政安排如请假的政策、补堂安排。家长则视乎他们对子女的期望、对教学风格有否特定偏好、有多关心进度之类。
年纪愈小的学生,我就愈需要与家长站在同一阵线,尤其四、五岁的学生。有时候家长在场旁观,与家长合作课堂能更加顺畅。但比较想表现自己的学生,注意力可能会放在寻求父母认同,反而比较难集中。有时候家长和我共同教学,小朋友也有机会尝试挑战权威,或者故意不服从。
对不少家长来说,小朋友有否“失礼”是个重要的事情。四、五岁的小朋友喜欢探索,不会全按着指示学习钢琴,而家长有时会在意自己的小朋友“唔比面”(不给自己面子),比如在琴上用拳头乱按,又或者是故意用相反的次序弹奏音符。很多家长问,“是不是每个小朋友都会这样(不听指令、乱按琴键)?”
爱子心切,或许每个家长都会担心自己的小朋友是不是特别不听话、很“难搞”,或者担心自己的儿女为他人添了麻烦,表示不好意思。这些问题背后,可能是家长想知道孩子是否正常发展,或者担心孩子学得不好。事实上,我早就习惯了学生在课室上扮猫、扮狮子,问我能不能做拱桥和倒立,或者试图用手肘或鼻子弹琴,不断即兴弹奏说要教我怎样弹、叫他试弹A音却刻意弹C音试探反应。
只要小朋友来到,人还坐在琴椅上、用双手弹琴,我都不会感到特别惊讶或难处理。我当然会尽力引导,但他们不跟从指示,也是意料之内,这是他们成长的过程,时间久了自然会有所改变。如果他们四、五岁,却完全听命于我,甚至表现出很害怕不听话会被责骂,我反而会好奇他们是不是有不好的经历。
其实老师的主要职责,正正是面对眼前的小朋友,观察他们对指示的反应,思考怎样引导他们,建立音乐感和肌肉记忆。我不会期望学生要听话、有礼、尊师重道,那些都是大人的礼仪,来到琴行最重要是给予空间去探索和尝试,用最适合的方式教学。我才不会认为他们失礼甚么的,小朋友不听家长或老师的话,也不等于家长没有好好管教。
我曾遇上一位五岁的小男孩,每次上课都不会回应我的说话或者跟随指令弹琴,而是不断做其他不相关的事情,或者把话题拉到别处。我最初也暗自焦急,每节课用不少时间试图让他乖乖按指令学琴。后来我又教他新的歌曲和乐理知识,但感觉对牛弹琴,他还是照旧四处走动、问各种不相关的问题。
但过了一段时间,他忽然回到钢琴前,用正确的方式演奏了整个乐曲。这让我明白,即使他可能完全没有表现出在聆听,甚或表现得不感兴趣,课室上说的话他都有默默吸收,他想要回来弹琴是就能够运用所学。于是我每节课都照样教授内容,减少跟他拉据,尽量输出教学内容,等到某一个时刻,他可能又会忽然进步。
我从中学会,有没有“听我讲”的执着是可以放下的,最重要是他对钢琴有兴趣、学习也有所进展。

现实烦心事
说了那么多梦幻的话,也说说比日常上课所见更现实的事——薪金与稳定性。教琴是手停口停的工作,学生来了就有学费,学生不来就没有。
一年五十二周,学生时代最期待的暑假、打工仔最期待的圣诞、新年,是自雇教琴老师面对学生请假甚至流失的时候。我本身已是斜杠族,对公众假期没太大兴奋感,教琴之后,更是抗拒长假期。我有时会干脆先发制人,预先在学生大概都不来的日子请假,好让心理好过一点,制造“是我请假不是你们请假”的感觉。于会乎,再多学生也好,一年到头总会有一两个星期没工开,这段时间找其他短期工作帮补,又不是易事。
虽然教琴时薪高,但黄金时段给了教班,基本上当天很难安排其他固定长时间的工作。我最初教琴,因有其他较固定的兼职帮补,加上教琴初期学生数量少,收入本身就不多,学生请假也没有太大影响。到后来教琴占工作组合的比重更大,面对两星期内大部分学生都请假,确实会感到焦躁和不安:一方面失去平时生活的规律、节奏,另一方面看着收入减少,更甚的是怕学生停了一两个星期没学,失去学习热情。
身为钢琴老师,我怕学生流失,也同样在心底里面害怕自己会泄气。
跟所有职业一样,日子久了,难免会碰到烦心事。再珍惜与学生的点滴也好,好些时候付出是不会得到回馈的。又或者说,用心教学是我的事,学生学不学、学得如何是学生的事。有很多的不辞而别、学生冲口而出的言语,也会让负面情绪累积。到学生请假的时候,有了空档,那些灰心与冷意就好像找到空间去浮现。
教琴数百元一堂,没有想像中的好赚。只叫学生“自己弹一次”,再指出错音作罢的老师比比皆是,而有心的老师,习琴十数年,不断摸索教学手法和持续进修,所花的时间和专业性,也绝对值得一份能够糊口的薪水。“一千元一小时的钢琴老师”只是特例,这个行业里多数老师需要同时承接不同类型的工作维生;即使花上一两年在琴行累积学生或自行招生,也始终无法解决薪金不稳定的结构性问题。
更甚的是,要有更稳定的薪金,又或者新晋琴室需要在市场生存,也难免要迎合市场需要。教国际学生或许能以兴趣为先,但相对于一些旨在考级的本地学生,前者的退学率较高,累积稳定学生群需时更长,后者则因为要考级,不会轻易退出,自然比较容易留客。

I want you to be happy
直至我开始教琴前,钢琴就像我人生的布景版——抬头一看,他从来都在,却从没成为过人生的主轴。入行时我全不抱期望,做着做着发现不错,问我为甚么教琴的话,除了是对钢琴的喜欢,还因为在教学中收获了种种缘份和自我启蒙。
自出生,家中已有一台钢琴,两三岁时我便会自行尝试弹出听过的歌曲,到三四岁便开始学琴,一学便学了十三四年。因着少许天份,音乐成为我小时候的优越感所在,总是想要表现自己,收到赞美就会沾沾自喜。长大一点,直到中四、五,我总是把握在校内弹琴的瞬间,暂时脱离群体社交,专注在当下的演奏获得一丝平静。
学琴十数年,前面至少十年,我都不明白音乐是甚么,只是按技巧在琴键弹奏。事实上,那些年长期被学业压得喘不过气,处于心灵麻目的状态,不要说用弹琴表达自我,很多时候连自己有甚么感受都不知道。
转捩点是中五的一次演奏级考试。那次考试不合格,考官在纸上写上“技术上达标,但听不到任何音乐”。我才第一次直面音乐是甚么,迫着思考在练习技术之余,自己想透过音乐表达甚么。
重考那次,考官在开始时跟我说,“我想你是开心的(I want you to be happy.)”,说我可以想像自己在开音乐会,而他是观众。就这样,我重考合格了,自始弹琴对我来说再也不是追求好不好听,而是心灵触动和连结。后来我去旅行看见公共钢琴,又或者在本地咖啡店看到钢琴,都会上前弹奏。曾有咖啡店主跟我说,有很多客人听到弹奏的音乐都哭了,当刻忽然明白:比起得到奖声,有人听了我弹奏的音乐而感到治愈,才是真正让我感到满足的事。
现在我教琴,有时仍想摸索自己还有多少演奏的渴望,还是只想要为他人保有学习演奏的空间?唯一可以肯定的是,我想诚实面对自己的渴望:我和那些弹完一首歌,转头看着我的学生如出一辙,内心都住着一个想被认同和被理解的小孩。
(为保护学生隐私,文中提及的学生故事经修改和模糊化处理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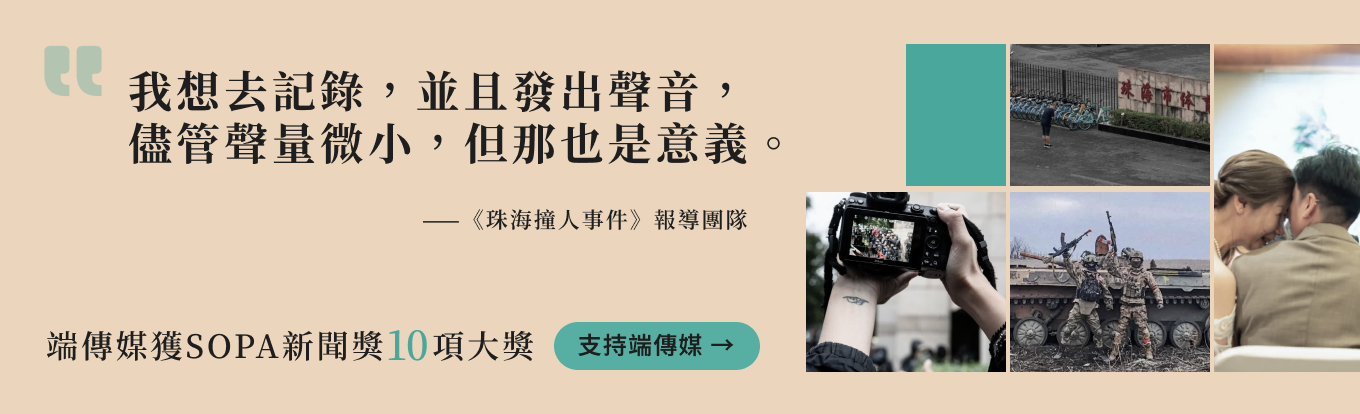



我讀你的文字很有被觸動的感覺,因為你很真誠地坦露你的想法,而這些想法往往令我感到很溫柔。